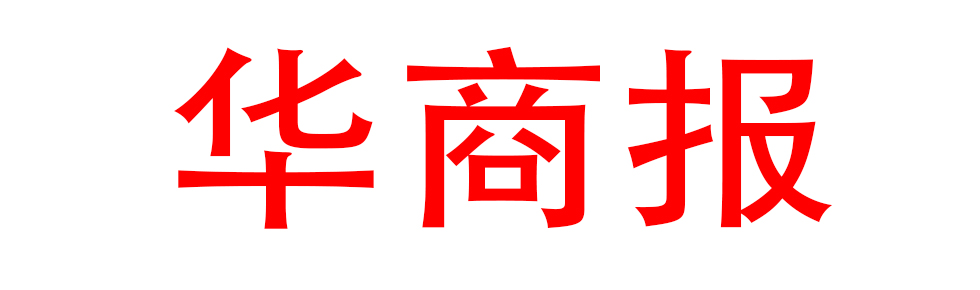“神经内科有很强的逻辑推理性,每次看病人就像破案一样”杜翔说,杜翔是年的,他于年医院工作,至今已有24年,在这24年里他从住院医生到主治医师,再到副院长,有太多的故事......
在不识字的年纪就见了许多药的名字
杜翔的父母都是医生,杜翔小的时候,父医院工作,可以说,医院长大的。“再有就是在药房里陪家人值班,看着那些药瓶认识了好多药名”杜翔说,从小深受父母影响的他,对医生这个职业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所以高考时也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医生,“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摔倒了,周边的人说‘那是杜医生的孩子,医院’,我当时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是比较受人尊敬的”杜翔说。
把坏台灯当作练习打结的工具
杜翔从大学起就想和他父亲一样,当一名外科医生,他也一直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。“我当时为了练手,就把舍友坏了的台灯当作练习打结的工具,练习到最后,相当于给台灯织了一个套”杜翔说,医学生在宿舍里缝手套、缝葡萄皮都不是网络上凭空造出来的,而是他们实实在在做过的事情,杜翔也不例外,凭着这股勤奋劲,杜翔在校就拿了很多个第一名。但事不遂愿,在招聘时,由于他戴着眼镜,招聘的老师认为他更适合内科,于是他于年去了神经内科。
“刚到内科时,说实话我是有点郁闷的,因为我喜欢动手,更想当一名外科医生的,突然成为内科医生,一时真的有点郁闷”杜翔说,但他很快就想明白了,“神经内科诊断有很强的逻辑性,就像破案一样,危重患者多充满了挑战,让我逐渐安下了心,更逐渐喜欢了这个专业”杜翔说。
令他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在年的时候,他有两个重症病人,一个十几岁的孩子,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,“当时我们一直守着他们,我们老主任给患者熬的鱼汤,我们一有空就陪着患者,让他减少恐惧,我们还给那个孩子买了他偶像的磁带......那个孩子上了大概40天呼吸机,每次的情况变化就是我心情的‘晴雨表’,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,能做的都做了,但最后还是没能治好他,我既自责,又无助,第一次感到了无力回天”杜翔说,这种失落感使他受到了不小的打击,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另一个年轻人康复了。
杜翔回忆到,那个年轻人几乎把那个病的各种症状都得完了,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,这个年轻人康复了,“现在偶尔见到他,还给我打招呼呢”杜翔说,“有时候,你尽全力去救治,最终没能留住患者的时候,那种失落感对我们的打击很大,更加让我们敬畏生命,同时,医治好一个患者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舞,也是这种鼓舞让我们可以一直坚持下去”杜翔说。
医生、医学生、父亲来回切换
据杜翔回忆,他刚开始当医生的那些年没参加过同学聚会,因为每次聚会时他都在值班,“我们是连着值班,每年大年初四、初五同学聚会,我都在值班,没办法参加同学聚会”杜翔说。
年他正在读研究生,当时的他既是学生、又是20个病人的医生、还刚刚成为父亲,三重身份使他喘不过气来思考其他的东西,“医院,晚上写完20个病人的病例后,马不停蹄的又开始写论文,当时孩子刚刚出生,所有事情赶到一起,忙的焦头烂额”杜翔说。
谈及自己的家庭,他称,他的妻子也是一名医生,两个人工作起来经常会忽略家庭,孩子也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,“孩子还小的时候,一早醒来发现我们不在家,他一个人害怕,就会哭,最后孩子习惯了,也就没什么感觉了”杜翔说。
从零开始学着做一名医疗管理者
年杜翔成为了医务科副科长,当时他并不那么愿意去,在领导和老师的不断教诲下,才理解了,“当时的我想当一个好医生,这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,如果做管理,我可能要把时间都分一半出来,所以我当时很矛盾,最后是老师告诉我,做了管理,你可以让团队变得更好,之后可以救治更多的病人,就这样我才逐渐接受了这个职位”杜翔说。
成为科室副主任之后,他更多是作为老师,在学生的旁边指导学生,让他们安心,“因为我刚开始当医生时不怎么自信,老师不在的话会有点无助,甚至是害怕,害怕出错,我很能理解老师对学生的意义”杜翔说,这之后,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管理者。
“想明白了以后,我就开始学习管理方面的东西,因为当医生是科班出身,管理是没怎么接触过的,得从零开始学习,一边看相关书籍,一边摸索怎么能让团队变得更好”杜翔说,在一代一代人的努力下,医院由最初的张床变成了张床、面积也不断扩大、甚至在寸土寸金的地方给医生们一层楼作为培训中心……这都是他们所有人不断努力的成果。
每周不去病房就不舒服
从科室副主任到医务部负责人,再到副院长,杜翔介绍到,即使他再怎么忙碌,也会坚持去查房、坐诊等等,“我一般白天开会,下午查房,每周保证一定的坐诊时间……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,每周必须得去病房,不然老觉得不舒服”杜翔说。
在十四运火炬传递活动上,他作为咸阳第四棒火炬手倍感荣幸,这是因为他在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,带领22名队员进驻隔离区,救治患者53人,完成了救治任务,“能作为卫生系统的代表成为火炬手我觉得非常光荣,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肯定,让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医务人员的自豪”杜翔说。
华商报记者杨宁编辑牛佩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