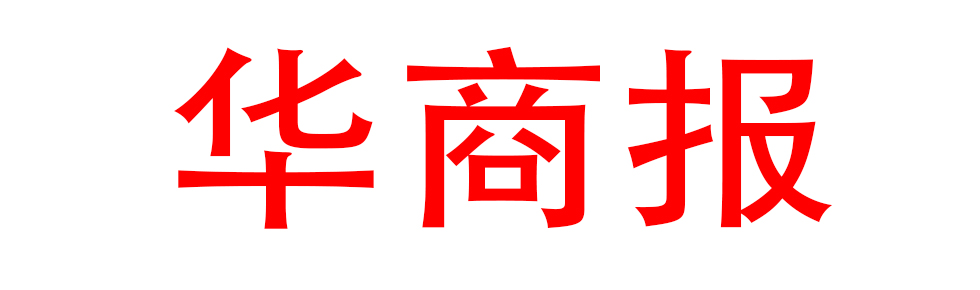我的母親
文/杜埃
年,我離家多年後回到了粤閩邊上山城——大埔縣莒村故鄉。當我回到縣城後,那時還没小汽車,縣的領導要我走新開的公路和坐上剛通車不久的長途客車(客車要經過我村向湖寮區駛去)。這時我猶豫了:坐車還是走路?結果選擇了走路。讓嫂子和大侄女先坐車把行李運回去,我則和隨行伙伴易準同志步行。從縣城到我村足有40華里,中間還有幾段陡斜的山路,必須喘着氣上崗下山。
“何必呢?”縣裏的領導説,嫂子也勸。我還是一意孤行。爲什麽?因這條40華里的路,上縣裏的初中唸書時,跟同學們來回步行過多次,哪個山、哪個坳、哪個凉亭……都記憶猶新,重走一趟饒有意思。
果然如此。走了35裏老路,勾起了許多少年期的往事和再見了一個個山村的面貌。再走幾裏,就行近故鄉時,我的心情慢慢緊了。經過大嵊坑那個山邊田垠,我想起孩提時看見母親在小禾場上用絞架夾着稻把打谷子,嫂子則把谷子挑回村的情景;經過糧腹垌、虎豹案時,腦裏浮泛起小學放暑假時我挑上竹籠裏的小鴨子跟上放牛的外祖父,把小鴨放進剛收割過的田裏去找谷子吃的情景;大嵊坑的黄屋村有些屋子塌了,有些是新建的,但過去那間私塾小院一棵古老的桂花樹却仍然挺立,盡管蒼老多了。
走過風雨亭,便可看到我村子的一角。它在我腦中出現,使我的心立刻緊縮,怦怦跳起來。啊,闊别多年的故鄉家在前面,它的容貌怎樣了?我們家族的人和鄰里又怎樣了?還没走進村子,却泛起許許多多昔日的情景,心情起伏不停,脚步也放緩了。真是“近鄉情更怯”。
啊!一群人擁上來。真的,我真的回到了故鄉!心裏想:要不是全國解放,遠去的遊子真不知何時何日才能回來呢。
故鄉經過八年極其艱苦的抗日戰争和緊接着三年的解放戰争,似乎江山依舊,人事却有了很大變化。首先是北山我家左邊的山崗上立起了一座不大的紀念碑,那是爲解放戰争時期幾個犧牲者樹立的。隔着莒溪水西南面高大的馬山增添了不少墳墓。客家人很敬重祖先,墳墓修得特别講究,全用石灰、火磚砌成,白墳一小座一小座點布在山坡上。村中60歲以上的老男人没剩幾個,老太婆多些,許多人已離世而去,大半是抗戰時期餓死的。小學老同學留村的也没幾人。他們都爲了生活,遠走他鄉,或者漂洋過海到了南洋。我接觸到的都是不認得的年青人。“少小離家老大回”,却被青年們邀去開座談會,會上我講瞭解放前村中情况,這裏面充滿激動的往事,暫且不去説它了。
最令我難忘的,是一個微微傴僂的背影。這背影無時無刻不緊緊縈繞在腦際,特别是每當我一次又一次走過我家的自留地時,這個身影在菜園子裏鋤地,或播種,或除草,或摘菜;她穿的是舊式藍布女服,默默地在那兒勞動。她,就是我的母親。
我的母親姓陳名汀,是同村隔一條小山坑的貧農陳國材的二女兒,我父親是個華僑店員。據韭婆説年青時她長得苗條、漂亮,人勤勞,又合得左鄰右舍,是被我外祖父母稱爲賢惠的一位村姑娘,外祖父母把她當成掌上明珠,很疼她,但她並不因獲得寵愛而嬌縱慣性。她生性寡言,性格恬静温和,從不招惹是非,肯關心人、幫助人,博得娘家許多人的贊賞。嫁過來後,她的美好的品格也受到左鄰右舍的讚揚。我父親大約20歲左右從南洋回來娶了她。這裏有個小故事,也是韭婆告訴我的,當她嫁給我父親時,父親因她長得漂亮、賢惠,新娘轎子到家,向族裏的人各各奉上茶、鞠躬之後,父親揭開她的鳳冠和面紗,携着她在我們這個只有三個小姓聚居的田背角小自然村轉了一圈,向鄰里們行見面禮。這在當時的習俗看來,是頗爲新奇的。我父親因在南洋生活,思想比較開化,也想借此炫耀一下自己娶了個大姓人家美麗的姑娘。這一來,却給鄰近開個小小裁縫作坊的人看了個清清楚楚,患上了相思病。後來爲了生活,父親又只身遠出南洋,抛下妻子和生下的兒子在鄉中耕田過日子。那個小作坊的老闆認爲有機可乘。讀者可能知道,客家人聚居之地都因山多田少,結婚後老婆有了身孕,便又再去南洋謀生。一去十年八載未回。那個小老闆便借故常來糾纏,都給我母親推得一干二净,被鄰里們傳爲佳話,而那個男人却留下不少笑柄。
幾年後,父親在南洋山邊裏開了個“鴉搭店”(用杉枝搭蓋的小屋店),母親和外祖母便由村中的水客帶去南洋,跟我父親聚居多年。待我小學還未畢業時,父親寄回一張外祖母和我父母親合照的照片。外祖母和母親都南洋化了,梳裝打扮,穿上黑色長裙,我這時,才認真瞧了瞧母親的容貌,果然她長得很美,楚楚動人。
又過了若干年,小“鴉搭店”倒閉,父母雙雙帶上小弟又回到了山鄉,過着接近中農的耕山種地生活。這時正好是中國鬧第一次大革命。離我家僑鄉50多華里的大寧鄉成爲農民運動的中心。不久,國共分裂,清黨清鄉開始,殺了不少農民知識分子,也有不少逃到南洋去。那時的一天的深夜,大約是十一時左右,忽然有人從屋背山上躡到我家敲門。母親隔門問清是誰?回答是“大寧同宗”(大寧多半爲我家遠房同宗),父親便急急開了門,那時正是風聲鶴唳、人心惶惶。我村小學的革命老師都連夜逃亡了。原來這五位大寧同宗也是躲避捕殺而上了山,不敢走大路,在山上餓了幾天,然後一山又一山於夜間逃到我們家。這裏面某一位“梓叔”(鄉里人的宗族觀念是很强的)在南洋認識我父親,相交不錯。他那時回了國,也有時到我家作客。母親忙把大門閂好,父親問明情由,母親當即殺了三只鷄,煮了大鍋粥,熱情款待,到了凌晨二時左右,我母親義無返顧,戴上竹笠,主動親自帶領這五位逃亡者上後山,走過半山上的黄湖堂村,轉到水和蓮村、密坑等山地,急急忙忙一夜走山路,最後把他們帶到梅潭河邊,雇了一只小民船下潮汕,逃到南洋去了。
母親於第二天上午才回到家裏,一再叮嚀我這件事不能告訴任何人,否則,全家大禍臨頭。其實,昨晚上父親就已鄭重告誡我了,而我那時也已有點兒懂得我敬愛的小學老師爲什麽一夜之間逃跑了。我開始有了憎恨……
年,内戰激烈,而農村到處破産,青年没出路,仿徨苦悶,不可終日。在縣立初中輟學後,我當了原村小學半義務教師,昔日那些老師不知去向,找不到光明。我看了老師們逃亡前秘密藏下來的大批革命小説,還有看不懂的布哈林著的《共産主義ABC》,特别是看了蔣光赤的《少年漂泊者》,引起極大的共鳴,决心離開破落而死寂的山村,和兩位同學毅然到廣州流浪去、漂泊去。父親大不以爲然,因他想强迫我和童養媳結婚。他還拍了桌子,動了火。我没理他,而向來疼我的母親却截然不同。她噙着眼泪,從木箱裏取出一枚捨不得用去的當年結婚戒指,塞進我的手心,緊緊握着只説了一句:“你去吧!”
年冬,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華北,民族危機越發深重,北平學生在黨的領導下發動了震動中外的“一二·九”運動,跟着全國各大城市支援。春節前我參加了中大學生的下鄉抗日宣傳運動,到汕頭、潮州,最後回到山城大埔縣。我離村後第一次和隊伍回到了故鄉,我的母親正患哮喘病卧在床上。她從蚊帳裏伸出瘦骨嶙峋的手,撫着我的頭,傾訴了思念,見到我回來,非常高興。而我們日夜要趕排抗日話劇,以便在村裏公演,在家時間不多,也没跟母親好好多呆上點時間。
公演完,即接到廣州留城學生繼續示威,發生了“荔枝灣慘案”的消息。全隊隨即離鄉趕返廣州。母親聽説後把原來準備在春節宰來還肉鋪賒賬的猪宰了,把猪肉最好的部分加上藥材炖了給我們餞行。
因工作需要,我於年到了菲律賓,做華僑抗日宣傳工作和國際宣傳工作。當時國内反共高潮迭起,到海外去的人都不聲張,準備立地生根,做長期打算。因而我的出走,也只是極少數人知道。許多原在一起工作的朋友却一無所知,都認爲我失踪了,有人傳説我已被捕被殺。這件事傳到當年已由香港回到内地參加抗戰的李育中耳裏(現爲華南師範大學教授),也以爲是真的了,爲了紀念,他在長沙某報寫了悼念文章。而消息又誤傳到我的山村,父母悲不成聲,因已成了“匪屬”,便只能忍聲吞泪。在極少數人知道的情况下,母親秘密設靈牌於她的卧室中(那時是不敢把亡人靈牌放在廳堂上的),每天燒香供奉。以上這一切,是樑上苑同志於太平洋戰争前兩個月到菲律賓告訴我的。並説:“這個誤傳很好,不必去澄清,也别告訴你父母,這對工作有好處。”過了一個多月,我反復考慮,應該設法帶信回鄉,説明還活着,但不告知地點,而且信可寄到湖南轉寄故鄉,這不就是很穩當的了。但那個時期正準備辦大報,國際時局又緊,工作很忙,還没待執筆,太平洋戰争突然爆發了,與香港、國内一切交通都中斷了.
這件使我母親終生含恨的事,一直待我於年回鄉時,和母親的結拜姐妹韭婆見了面,聲泪俱下地告訴了我。果然,上苑所告的是事實。因爲抗戰時期的大饑荒,廣東出現不少萬人坑、萬人冢,我的母親也在那個年頭因飢餓貧病而死去。
要是那時我來得及用迂逥的方法告訴家裏我還活着,母親會有多大的高興啊!即使她死時也會放下一樁沉重的心事。
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母親,每個母親對自己的兒女總是無限慈愛,總是在盡自己的一切來撫養兒女,讓兒女長大成人,我的母親也如世上許多善良的母親一樣。想不到“一二·九”下鄉宣傳那次見面,竟是最後一面了。然而,雖時隔半個多世紀,我母親那崇高的形象,始終還活在我的心裏!
杜埃照片
作者:杜埃(莒村田背角人)
作者简介(来源网络):
杜埃(—〕,原名曹传美。笔名杜洛、T·A。广东大埔湖寮莒村田背角人。杜埃的文艺论著和文学作品计有《初生期》、《人民文艺说》、《论生活与创作》、《乡情曲》、《不朽的城》、《花尾渡》、《杜埃散文新集》、《丛林曲》、《冰消春暖》、《风雨太平洋》(上、中、下)、《杜埃杂文集》、《诗集》等10多部。童年在村内养正小学读书,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大埔中学,由于家境贫寒,三个月后辍学回乡任小学教师。年8月,杜埃病逝于广州,享年79岁。
年流浪到广州,与人合编《晨曦》,在《民国日报》文艺副刊发表第一篇小说《私娼》。年考入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系。同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。担任过《火花》等地下刊物的编辑。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抗战爆发后,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任代理宣传部长,同时主编《大众日报》文艺副刊。年到菲律宾做抗战宣传工作,年回香港。后任《华商报》副总编。他的杂文揭露、抨击旧社会的丑恶和腐败,文笔辛辣。
解放后,担任中共广东省委文教部、宣传部部长。写了不少文学理论文章。还创作了一些富有南国情调的散文。创作长篇小说《风雨太平洋》,表现菲律宾人民和华侨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生活。担任过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、省文联第一副主席等职。
文章来源:中国评论新闻网
杜埃所有赞赏以莒村